講座側記|三城故事:探索跨越邊界的遊牧生活與藝術旅程
- 星濱山 ZhengbinArt

- 2025年4月28日
- 讀畢需時 10 分鐘
2025年三月,星濱山的藝術進駐空間SPACE MOOR迎來了第二位法國藝術家Clément Denis和他的太太Fouzy Denis,而這是一段超級不可思議緣份的展開。Clément Denis是受到台北白石畫廊的邀請而有來台的計劃,但同時也是他做足心理準備,要暫離法國開始向外連結的一年。隨著進駐期間的會議,我們也找來在九份致力於地方活化的朋友林孟萱(Really)擔任翻譯,聊著聊著發現彼此的共通點和在意的事情十分契合,這場對談就此萌芽,本篇將會記錄當天現場的對談重點。

台北白石畫廊隆重推出《Beyond the Lines, Where Borders Collapse II》藝術家Clément Denis首場台北個展之延伸對談活動 —— 「三城故事:探索跨越邊界的遊牧生活與藝術旅程」。此次對談集結來自法國、台灣基隆與九份的三位創作者:法國藝術家Clément Denis、策展人和地方行動者林書豪、語言與文化推廣者林孟宣,從「遊牧式人生」出發,探討藝術、文化、社群如何超越疆界、深耕在地。
此次對談將聚焦於以下核心議題:
● 遊牧主義與文化實踐的關聯
● 藝術與社群如何彼此滋養與共構
● 打破東西方邊界的藝術社群可能性
三位講者分別活躍於巴黎、基隆與九份,以各自經驗探索在地與全球之間的創作縫隙。從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、正濱漁港永晝海濱美術館、到九份美代子理髮廳保存計畫與語言文化再生行動,本場對談將是一場關於邊界、文化流動與藝術實踐的深度交流。

PART 1|自我介紹、游牧生活與文化之間有什麼樣的連結?
Clément:提出游牧主義、移民的提問,所以選擇紐約作為第一個展出地。
白石藝廊邀請來台灣展出時,感覺台灣是很適合的第二個展出地,因為擁有移民等歷史背景。
在白石藝廊的展覽分成三個主要的部份:當代、逃脫、搏鬥,我們在不同情境之下尋找我們是誰,並長大成人。
巴黎對我而言,不是一個對發展個人非常健康的地方,因為疫情反而有重生的機會,來到了這裡,並繼續發展這個系列的創作。
我認為文明與藝術不能分開,一直很希望藝術可以走入城市、走入生活中。今天現場有三位講者,希望可以展開一個討論,就是如何讓彼此能夠走進大家的生活之中。
Clément for 書豪:對於遊牧生活的看法、在日本瀨戶內的經驗分享?
書豪:我叫做林書豪,現在是在基隆的正濱漁港,我們團隊在當地進行藝術參與和策展,進行當地的活化。想先反問Clément一個問題,我自己在日本藝術祭待過一陣子、當過志工的經驗中,知道要熟悉當地成為當地的一部分,其實需要習慣這個環境一陣子,想問在這樣還沒有習慣的過程中,有沒有遇到什麼樣你覺得特別難以接受的部分,在飲食上、在語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有沒有特別難以接受的部分?
Clément:對我而言,當我決定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,已經決定要接受所有。當然有不一樣的生活習慣、有生活的差異,加上在我剛到的時候就有很多的事,但很驚艷大家的友善,我感到非常地感動。
書豪:回到原本Clément的問題,我在瀨戶內兩個月的時間,在文化差異上給我蠻大的體會,我在體會日本事實上跟藝術祭和地方的連結的過程是如何推進。也會反思我回到台灣後,我會怎麼樣來做這件事,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發生影響力。
書豪for Really:你並不是當地人,為什麼選擇去到九份行動?
Really:大家好,我叫做林孟萱,我本身的專業是英文教學,我在2023年才在台灣,這一年多兩年的時間在九份做文化保存跟地方創生。回應書豪的問題,我會這樣選擇是因為之前有在澳洲待過一段時間,去進修語言,在那裡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就是語言跟文化的關係密不可分,比如【龍】,在東方是吉祥、明亮的,西方則是灰暗、感覺有破壞力的。加上在澳洲待過8年之久。回國後發現,我其實並不熟悉台灣,有個很強烈想多了解台灣文化的想法。加上碰到在九份工作10年、本身是在地人的小嫻詢問可否幫忙,我就答應了。一開始也會對自己有懷疑,我和九份沒有什麼連結,後來我想到,我對台灣有很強的認同,但沒有特別對一個地方有歸屬感,那九份也是屬於台灣,而且當認真去認識一個地方的時候,會發現所有的事情都是連結在一起的,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還在這裡,還有在做的事情。
Question for 書豪&Really:你的職業如何與你正在進行的計畫產生共鳴?
書豪:本身是唸建築,所以關乎到人、空間,同時在反思如何把藝術跟建築結合在一起,因此我沒有成為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師,反而是在思考我們如何能在一個地方,去面對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去做改變,那我認為這是建築師的責任,同時也是藝術家用他的觀感去創造了一個地方改變的機會,所以對我來說,它是同時存在的,所以現在在基隆,漁港現在面臨轉變的過程,就相對很需要這樣的角色去推動帶來合宜的發展,以我的角色來說,其實我覺得每個人身上他有一定的專業,以及有他的興趣,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每個人的專業興趣為地方帶來改變的過程,其實是一件蠻不容易的事,因為我們的生活,絕對不會只有政府,也不會只有某些人的掌權,它其實來自於生活在這邊的人,謝謝。
Really:我剛剛有提到我的專業是英文教學,我認為語言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話,語言不應該把它當作一個學科,然後把它定性地拆解成很多的單字,所以其實我的英文教學跟我現在在做的事情,本質上都是相同的。我會問學生發生什麼事情,然後他跟我說怎麼樣,他跟誰去哪裡,比如說上個禮拜跟他去的,那這個動詞用過去事,就是會是用生活中的一切來學習語言,同時重點在於他跟我的交流跟分享,我也在跟他分享我的生活,我也在跟他分享我對於自己的觀察、對於地方的觀察,那這個相對的也會影響到學生,他會去注意自己的生活是怎麼樣,然後他會開始跟我分享他的生活,所以那包括說我現在在九份,我面對到的國際旅客,我們也是在跟他們分享九份是什麼樣子,所以其實我目前的兩份工作,不管是語言教學或者是地方文化推廣,都著重在交流上,把生活與語言結合。
Question for Clément:對於游牧生活和接下來的創作方向?
Clément:原本以為游牧主義只有等待、逃脫、移動,但我發現想錯了。我忘記了在生活過程中,創作可以幫助我往前進,所以創作是很重要的第四元素。
為了發展第四個元素,來到了台灣,這次想以身體作為切入,所以跟北藝大舞蹈系的學生翌婷開始合作。從身體的這個媒介裡面去發展更多,我想要在這個元素表達的是,如同我前面提到的,我的創作是來自對於移民跟兩件事情的提問,我認為在透過身體的創作中,可以找到我對於靈性、還有這些提問的解答,接下來後續的創作大家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,謝謝。

PART 2|在地脈絡下發展的藝術計畫,有哪些可能性與前景?
書豪:很開心今天大家來到白石藝廊,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實在台北不遠的地方,基隆大概十分鐘的車程,會來到離海非常近的地方,其實過去它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地方,在17世紀1926年西班牙從歐洲航海到台灣,到了基隆港做貿易,1942年荷蘭人又來到了這個地方,我相信在400年前至今,世界國家和土地的關係其實已經開始游牧,那回來講一講,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在這邊所做的事情,也是有一群游牧的年輕朋友,包含曾經在國外生活來到基隆這座城市生活的年輕朋友,以及來自台灣各地屏東、台東還有新北等來到基隆,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事情,大概就是希望能夠把地方的這些傳統產業轉換成藝術的基地,而這個藝術基地可以提供給更多創作者一個平台,包含說我們現在看到的,我們的gallery以及我們自己的select shop都是提供給不同創作者的型態,不管在創作上的展演以及在產品上的銷售,希望他不只是單純的在文化上的推動,其實同時也包含經濟的推動,以上是我很快地分享。
書豪for Clément:在基隆這個地方,我記得我們剛開始第一次見面的時候,聊到你很關心海平面上升,以及你自己的家鄉,也遇到了許多的課題,所以其實我蠻好奇想問,在基隆有沒有給你更多不一樣的想法或創作上的刺激?
Clément:創作比較是次要,最主要是想跟當地人、自然產生連結。在基隆這個有些工業的城市,確實看見環境可再生、發展的機會。當然也有看到污染、動物保育的問題在基隆看見了。這讓我想到自己的家鄉。對於西方社會的人來說,不會意識到海平面上升的問題,會覺得是落後國家才會碰到的問題。我的創作就是希望把這些課題變成切身的問題。
Clément for Really:在九份的計畫,對於上述議題是否也有切身影響、以及對當地的觀察?
Really:九份要做的事情很多,包含網路建置、美髮廳保存、礦山齊柏林等等。
年輕人在地方可以從各種角度去協助。另一個是小嫻的存在,不停告訴大家地方是有價值的,漸漸地大家會感受到改變,變得主動願意幫忙宣傳或提供需要的物件。我們在做的事情可以視為一種「行為藝術」,把大家拉在一起去反思各種議題。打破疆界上,想挑戰的是打破時間的疆界,把過去的礦業歷史帶到現代人的記憶裡,以及在地外地人的疆界(EX礦山KTV,邀請大家一起唱歌),還有打破想像的疆界,想要打破自己的想像,想像九份未來、自己的方向,不會只限縮在現在。
Really for書豪、Clément:在九份,藝術駐村有可能被複製嗎?
書豪:比如侯孝賢,在尚未觀光前已經在當地做了許多類似藝術駐村的事情,所以這題回答很簡單,我覺得可以。居住地、旅遊地的中間值,也就是駐村這件事。九份要發生可以,唯一的重點就是來自於夢想山的這一群人,是不是能夠作為一個中介,以及有沒有類似像Clément或Fouzy這樣的角色存在,有的話實現的機會很高。
Clément:我認為可以離開觀光這個概念,跟一個地方真正有所連結,才是駐村的意義。1-3個月的駐村,可以打開感官、認識在地社群、想學地方的語言,也可以激發創作。在科技進步之下,想自在移動已經不是難事,對於自我的追尋,才是在科技進步之下,需要追求的意義。
觀眾for Really:異地人如何融入九份?如何去調和觀光與在地人的期待?
Really:因為有在教學英文,所以對於國外旅客和在地人溝通上都很順暢。
因為有小嫻的存在(已經深耕地方多年),所以加入時的阻力相對小很多。以及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幫助地方的。

PART3|我們可以如何跨越界線,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建立藝術社群?
Question for All:接下來幾個月,有什麼樣的計畫?
Clément:接下來5-7月在正濱遊客中心會有一場展覽,7月會到日本的白石藝廊展出(展出對風元素的刻畫)。8月在基隆SPACE MOOR展覽(法台鳥類、漁網再生)。
書豪:我想分享一下,上週末去了一間50年的漁網店,老一輩過世,留下很多漁網,這些漁網材料雖然過去產業很需要,比如說它是維生的材料,現在在角落變成遺棄的材料,但過去是很適合來發揮,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……,我相信Clément未來運用漁網進行創作會用得非常精采。
Really:每三個月辦一場市集、礦山齊柏林計畫、建立九份入口資訊平台。最大的夢想是在九份「創造生活」。現在就像大家看到的,大多是觀光區,生活機能已經越來越少,在九份,你找不到菜市場、找不到全聯、找不到超市,那所以我們想要的是能夠再把生活找回來,讓人們可以真正地留下來,因為有人才有生活,有生活才有文化,有文化才有靈魂。
Really for Clément、書豪:如何把大家串聯起來?
書豪:有個朋友分享,金瓜石有房子,但(房子)民宿本身已無法再經營下去。所以如果未來有朋友想住在金瓜石,這是個很好的機會,去交換、進駐等等。我們常常在游牧的過程,真的需要短期的宜居空間,老實說,不管我們未來在旅行上還是在駐村上,一定都會面對到你進入之後得有地方可以住,所以照這個問題來說,我覺得已經可以開始思考如何跟在地連結更多有趣空間、生活空間,你才有辦法去拓展這個地方的探索機會,相同道理,九份過度觀光,在無法選擇經營民宿的選項裡面,或許這個合作就是很大的機會。
Really for Clément、書豪:對於小嫻的私人博物館,有什麼活化上的建議?
Clément:我想到某位博物館學家,對博物館的詮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,非放在玻璃櫥窗內展示,而是讓作品跟觀者間有個良好距離,像是劇場一般,有觀看上的呼吸和想像。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是,博物館也展出生活的器具,打破了一般要是藝術品才可展示在博物館的既定印象。博物館要存在故事跟歷史,讓故事在空間中能夠持續下去。也讓我想到一位人類學家分享過,當我們進入一個地方中,也會產生人類和歷史上的變化。
觀眾 for Clément:想了解會怎麼把漁網應用在創作中。
Clément:我一開始的創作使用的是紙、畫布,目前的想像是用漁網去重新編織成可以乘載畫作的平面。但因為還沒開始,所以一切還是想像(笑)。
觀眾 for Really:我有兩年半在時雨中學讀書,金瓜石還保留地方的紋理和情緒,九份則是很觀光,團隊計畫如何串聯這兩個迥異的區域?
Really:九份、金瓜石、水南洞對我來說都是礦山,沒有特別區分開來,金瓜石那邊還有「礦山進行曲」的在地大哥大姐團隊,跟他們的距離也很近,我們所謂的串聯是資源上的相互幫助,但各個地方各自的特色還是都是各自地去保留,所以串聯上比較沒有問題。

紀錄|陳虹儒
攝影|徐莉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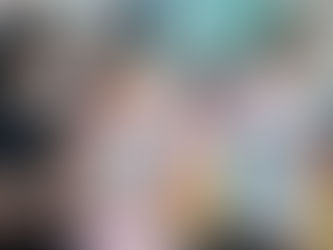




留言